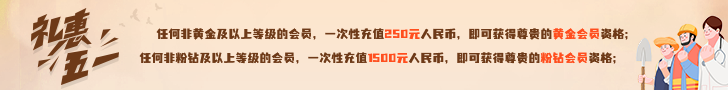人有一颗心 人有一颗心
章节字数:6545 更新时间:09-10-22 08:24
人有一颗心
寄萍踪
七六年的四月,梅俞溘然而逝,那年,他七十四岁。
一辈子的苦难也终于走到了头,人死了,现实也就拿他无可奈何。横加在他头上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辞和粪土,也就失去了任何意义。因为,他已感觉不到了,即使鞭尸,也仅仅只是活着的人的自以为是罢了。
好在人死了,没有灵魂;尚若有灵魂,可能这审查就会直追寻到地狱中去。文化大革命对任何阶级异己分子和不纯洁的思想及行为都有办法,唯有对死人一点办法也没有。所以文化大革命不准自杀,对于“自杀”者一律以叛党叛国自绝于人民来处制之,可见恨之痛切。好在梅俞是自然死亡。
梅俞戴着“右派和现行反革命分子”两顶帽子去世,他死在天快亮时。
他是突然死亡的,那天晚上十一点,他照例自我做了按摩,沐浴换衣,然后安睡,一切都正常。到得夜里三四点,只听得他叫了一声:“你们快来啊!”,也许不只一声,但听到的只这一声,等到家人涌到他床头,他已不动了。老妻着了忙,忙去叫院中的老校医。老校医到时,翻开他的眼睑,立即静默了下来。
哭声也就响了起来。
老校医是他儿子朋友的父亲,原是国民党的一个军医,也很艰难的过了一辈子。他对着梅俞鞠了一个躬,然后走了。
他走后,梅俞家里就乱了,开始忙着他的后事。老妻立即叫二女儿天亮去邮局,打电话,发电报,叫家人都回来。还叫她天亮后把梅俞的像放大一张,挂有墙上作遣像。虽然也知道不会有人来凭吊,但这似乎也并不是为了凭吊,只是一种应有的形式罢了。
谁会来凭吊一个现行反革命?在那种人人自危的年代。
这时,天已蒙蒙亮,二女儿正准备出去。那时,中心邮电局半夜也有电话,她刚走出门口,就叫了起来,说:“余伯伯来了!”忙迎了进来。这时,只见一个头发雪白,非常有艺术气质的老人走了进来,这人很清瘦,是梅俞的老朋友。但因文化大革命也已生分了的学院美术系主任,学院里唯一的一个教授余绾。对于余绾的来到,梅俞的妻子和家人没有想到。虽然梅俞五七年划为右派后,他们照常来往,两家晚辈都成了世交。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们就再也不来往了。当然也不仅仅是他,几乎所有的朋友都不来往了。对此,梅俞和老妻也常感叹:世态炎凉,人心不古。
余绾一来到,梅俞的家就一阵手忙脚乱,因为这实在是没有想到的,都以为他为了自保,早已不认了他们。没想到这么早,他一听到消息,就不顾一切嫌疑地来了。他握了握梅俞妻的手,走进内屋,来到梅俞床前,站在那里。他是一个早白头,自从梅俞家搬到学院后,孩子们再见到他时,他就是这样一个白头。如今站在梅俞床前,他的目光本十分明亮,现在却有点暗淡,面颊抽动了一下,然后对着梅俞鞠了三个躬。
走出内室,他在厅间坐了下来,和梅俞妻说了一会儿话,问了一些梅俞去世时的情景。遂慢慢站起,有点佝偻着背地走了。
余绾走后,梅俞家里的人就很有些感叹,因为在这样的时候,他能来看梅俞,是要有极大的勇气的,而且也表明了他心里还有着梅俞这个老朋友。
梅俞是五七年划为右派的,那时他在省文化局剧目工作室工作。此前他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一组散曲,并由《人民文学》编辑部加了个编者按,又由五六年的全国新诗选选了进去,因此在全国产生了一些影响。也许,就是这样,便有了些飘飘然。到了五七年,在那大鸣大放,引蛇出洞的年代,他参加了一次文艺界的坐谈会。在会上,发了言,说了些党要遵循文学创作规律的话,就被划成了右派。
到这时,他再后悔也是来不及了。
此后,他就一直为摘去这右派分子的帽子而努力。他下放去过省文艺界的农场,养过兔子放过鹅。但他为人愚直,不善于营钻,尤不善于走上层路线,便一直不能摘去这帽子,这在他是很痛苦的事。到了文化艺术学院后,常叮嘱自己的孩子,说:“如有政工处的老师来问你们,问我平日在家里干什么?你们就说:‘我平日里没事就学毛选’”。可见他对摘去这帽子的殷切。然而他是从不学毛选的,也没有什么政工处的老师来问过他的孩子。他就不知道,摘不摘帽子与他的生活态度是不相干的,很大一部分是在于领导对他的看法,而这却是他最不会做的。到了文化大革命,就吃了大苦头,因为他是死老虎。一开始就被关押了起来,不停地被批斗,挨打,受刑(比如踩夹棍)。后来又不停地转换改造地点,最后来到一个偏远县,那里有一个省文艺界的集训队。在那里,他又一次犯了错。因为到这时,他已很有些怨恨了,知道自己无论如何改造,也再也回不到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在一次愤懑之后,就在老人家的“要斗私批修”五个字上,打了五个大叉。又被别人所发觉,要知道,那时的集训队,每一个改造分子都是互相敌视着的,互相谩骂,互相扭斗,他就被揭发了出来。这样,他的性质就变得更险恶,到了定性的时候,就被定成了现行反革命,被押到另一个偏远县去接受监督劳动。这时,他已七十岁了。七十岁并不能为他带来什么,问题是他的问题很严重,被按排做最艰苦的工作——打柴,且每天要有一定的数量。他一个七十岁的老人,每天上山打柴,无论刮风下雨,都必得去。这样过了一年,在一个冬天,背了一大捆柴下山,跌倒了,把一条腿摔断,这样,就躺在医院里再也不能动。监管的人也没办法,打了个报告上去。最后等他的腿接好后,就断了他的工资,让他瘸着一条腿的回了家。梅俞就这样地回到了他这个极端困苦的家,差不多已是一个废人,还得接受当地居委会的监督。他无论在精神上还是肉体上,都得承受着极大的痛苦,他必得看着他的孩子们因他而受到牵连,或揪出,或批斗,或没有人生的希望。好在这次他这腿还真争气,就一直没有好起来,否则,又要被看押起来,送去进行劳动改造。
如今,他终于去了,而且是很平静地去了,也许是上帝也看不得他受到的这苦,于心不忍,给了他一个公平的交待似的。
他的家人在墓地把他安葬了,一个人也就这样,于世无干地只因某些人为的因素而被迫地交出了他只有一次的宝贵生命。
余绾,梅俞的孩子们叫他余伯伯。其实他比梅俞小十多岁,那时,也就五十多岁吧。他是一个油画家,且是一个印象派画家,他的画有莫奈的风格。但当时,印象派是作为一种腐朽的资产阶级流派在中国受到批判的,因而余绾的画就从未在中国大红大紫过,也就得不到人们的关注。但他的画却是无法否认的,尤其是在美术界,凡是看过他的画的人,都为他那高超的表现技法所震撼。他所画的画,是那么细腻而生动,闪耀着一片眩目的光,而且他的画还具有一种东方式的诗意和宁静,这是他有别于西方的地方。当时,一些苏联画家和国内的大家,都对他表示了关注和尊重。然而他却一直默默无闻。
他十分睿智,明理。解放后不大作画,也不大发表作品,却坚持着他自己的艺术理念。他似乎对社会有着较清醒的认识,所以在五七年时,他那时在武汉,又是教授,也参加了湖北那引蛇出洞的文艺界的座谈会,他就没有提一句意见,而是歌颂了党,因而被划为“可以信赖的红色知识分子”一列。后来来到了这个省,成了省文艺学院的校部委员,美术系主任。作为一个党外知识分子,这已是最高的待遇。
为什么这样说他,因为他并不相信当时的文艺思想。那时号召艺术界下工厂,表现工农兵,他被安排到一炼钢厂去体验生活。三个月后回来,来到梅俞家,对梅俞说:“画工厂?工厂里画什么?画钢铁?嗤,钢铁有什么好画的!胡闹!”他就知道对谁可以说真心话,对谁不可以。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也吃尽了苦,梅俞的孩子就看见他挨了打。也被关到了那省文艺界的集训队。
梅俞的孩子自然对他是极其尊崇的,尤其是老三。老三也喜欢画画,他崇拜他,倒不是他的地位,而是他的艺术和他那艺术家的气质。在这老三看来,余伯伯的画仍是中国画得最好的画,而且直到今天,他也一直认为余伯伯是中国第一流的油画家,他的油画,在中国,没人比得上。中国油画由于受苏联美术思想的影响,提倡现实主义,这在表现手法上,就大大地落伍了。余绾甚至嘲笑列宾,说他的画是“黄土加红土画出来的”。
他是一个稍瘦的高个,梳得很整齐的白发,长方型脸,清矍的面容,眼睛内陷,很有些西方人种的味道。看到他的人,会怀疑他是不是有着西方人的基因。他常穿一件有皮背带的吊裤,上衣塞在这吊裤里。平日里拿着一个大烟斗,他只抽烟斗,好象从不抽纸烟。就象一些西方画家一样。
这风度既儒雅又极其亲切,他为人又很低调。
他只和象梅俞这样的人及一些美术界的人来往,比如省师范学院美术系的徐晒,同校的彭秩以及远在陶都的戴凝,当然吴冠中也曾来看过他,按说吴冠中还是他的学弟。
梅俞下葬后的一天,余绾又来到梅俞的家。自从梅俞去世后,只有他一人来过。他向梅俞的老妻提出,他要去看看梅俞的坟。梅俞妻说:“还是算了吧,哪么远?”他却坚持。这样梅俞妻就陪着他坐郊区公交车去了坟地。那是一大片公墓,非常荒凉,但树木葱郁。下了车,在路旁买了些香烛,他来到梅俞的坟前。他把这些香烛点燃,朝着梅俞的坟拜了几拜,然后就站在那里,默默地没有说话,梅俞妻就流下了泪,他的眼圈也红了,却不说话,他就是这样一个非常平静的人。
俞梅的三儿子一直不明白,父亲何时交了这样一个好友?这已是几十年过去后的事了,直到去年,他才知道余伯伯去世了。一次和他姐姐说起这余伯伯,说现在在网上可以查到他,还能看到他的画。只是他依然被美术界遗忘着。他姐姐才告诉他,他们两家是怎样开始交往的。他姐姐是听他母亲说的。
那是48年的事,当时梅俞和余绾都在景德镇陶专教书,由于种种原因,在那年的冬天之后,余绾没有受到陶专的聘用,失了业。余绾的家境本不错,他父亲是国民党军队里的高官,好象是中将。但由于战争,失去了联系或是鞭长莫及,他因此就失去了一切经济来源,几乎是傍徨于人生了。在这样的时刻,梅俞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梅俞喜欢他的画,看重他。但这不是主要的,梅俞并不懂画。主要是梅俞这人向来富于同情心,看不得别人受难,再加上他家又有钱。现在看到余绾落难,就叫他住到他故里去,梅俞的故里在鄱阳。这样,余绾就来到了鄱阳乡间,梅俞叫家人给他收拾了两间房,安顿好他一家人。并在经济上接济他。
当然,余绾是一个不肯白吃人家饭的人。到了梅俞家后,就向梅俞提出,以梅俞在这乡间的关系,能不能把他介绍给这乡间的士绅,让他来给他们画像?赚一点画资。梅俞听后,觉得极是,就去为他游说。这样,乡间的士绅纷纷来找他画像。因此,余绾并不吃梅俞家的饭。但却出了一个问题,那时由于战争,就算不是战争,乡间士绅有财却没有钱。余绾给人画像,别人只给粮,不给现钱。有些甚至是现粮也没有,说好了等秋后,收了新粮才能给他。余绾有什么办法?为了生计,只要是写了欠条,都一一照画。
这样,又出问题了。他收的都是粮,没有现钞,而他的一切开支都要现钞。他就想把这粮运到景德镇去卖掉,换成现钞。这是一件很为难的事,那时没有汽车,都得肩挑车推,到景德镇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再加上兵荒马乱的,长途,又是运粮,这更是一件极具风险的事。这事梅俞知道了,就来找他,向他提出:“你这粮也不要运到景德镇去了,卖给我。我把我在陶专的薪水给你一些……”
在这样关键的时刻,梅俞又一次帮助了他。而且梅俞不但买下了他手里的现粮,连他手里秋后的欠粮也买下。这样余绾的生活才走上了正轨。当然,余绾也不是只卖画,他依然在向陶专求聘,梅俞也帮他说话。夏天过去后,他又接到了陶专的聘用书,然后开学就去了景德镇,恢复了教职。
可以说,这是余绾一辈子最落魄的时候。此后,他就一直在陶专教美术。过了一年就全国解放,他被调去了南昌,然后去了湖北,都当大学教授。后来,又调到了这个省。
他从梅俞故里走后,也是他所不能知晓的,梅俞这里却出了问题。当时,余绾在梅俞故里那穷乡僻壤画油画,在那穷乡避壤,哪里买得到油画颜料?好在他是个真正的油画家,那时的油画家可不是现在的油画家,他们几乎都会自制颜料。所以他在梅俞故里画的画,全是用他自制的颜料画的。还是由于条件的限制,他的自制颜料只能用当地的材料,也就不能达到真正油画颜料的质量。所以他画的油画像,过了一个夏天之后,就泛黑,变得非常难看。当地的士绅就不肯了,说:“这样的画,还能收钱!”要梅俞叫他回来理论,如不回来,就不对现。梅俞看看也是,不好意思要他们对现。梅俞的这种态度,助长了士绅们的态度,传开来,就没有一个肯来对现。好在梅家有钱,也是无可奈何,就把这些欠条全撕了。
老三听了这话,才明白老一辈人的友谊为什么那么深。就问他姐姐:“这,余伯伯知道吗?”
“这,我问过妈妈,”他姐姐说,“妈妈说,不可能知道。”
“哪为什么不告诉他呀?”
姐姐就笑了起来,说:“爹爹是怎样的人,你还不知道!妈妈又岂是哪种人?”
这后来的事余绾肯定不知道,他可能跟本就没想过这件事。不过,在他那样困难的时候,梅俞帮了他,这一点,他肯定记在心里。后来,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为自保,他和梅俞生分了些,那也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因为文化大革命实在是太残酷了。但他心里是一直有着梅俞的。现在他来看梅俞,既是友情,也是在表明一种态度,即,他永不忘梅俞对他的好。人心中的记得,是一种极其强大的力量,不管有着怎样的力量和权势,都无法阻止它。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它就不顾一切地表现了出来,甚至不顾一切的险恶。这是我们现代人所不能理解的。
又过了几天,余绾又来到梅家,这次他是和徐晒一起来的。徐晒是师范学院美术系的教授,亦是梅俞的好友。徐晒这人因和梅俞不在一个单位,不大来往,但却不生分。梅俞的孩子们都记得他,也许是不在一个单位,反而不大避嫌。他个子不高,总是戴着一顶法兰西式的那种小圆帽,叼着一个大烟斗。他们来到梅俞的家,这是梅俞去世后梅俞家来的第二个人。梅俞家人陪坐一旁。他们来到梅俞遗像前,站了很久,也没有说话。
我们不知道这沉默意味着什么?但这沉默显然意味着什么!
人有一颗心,这心又有着一种价值取向,人固然在强权面前不得不低下头来,而这颗心却永远不肯放下它的向往,它总是在顽强地在塑造着自我,以使自己有一个健全的人格。因为这是人生的底线。
随后,他们就坐了下来。也不谈梅俞,好象是在有意忘却。他们开始问梅俞的孩子们的生活。当他们听到梅俞家的老三娶了一个高干子女作妻子时,就很高兴。
余绾就问这老三:“你爱人姓什么?”
老三就回答:“姓余。”
余绾又问:“什么余啊?”
老三一时糊涂,不知该怎样回答,突然,他想起余绾不就姓余?就说:
“和你一个姓啊。”
“是吗?呵呵……”余绾和徐晒都笑了起来。
“你看我,”余绾笑说道,“连我自己的姓都想不起来了,姓什么都不知道了!”他说了这一句,摇了摇头。
梅俞余绾他们那一时代的真知识分子,有着一些纯自然的个性,不象我们现在的一些年青人,为了时尚而时尚,充高雅。梅俞余绾他们的儒雅是他们的自身和生活的一部分,是无法和他们的生命分割开的。他们不是去做出一种高雅的举动,而是他们的行为都是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的行为,是真自我——他们就是这样的人。
梅俞在五十年代也曾得意过一阵子,一次开表彰会,会上给他披戴大红花彩带,然后拥着他去跨街,这是非常荣耀的事。但他很不高兴,一回到家,一把把这彩带大红花撸下,丢到地上,用脚一踩,狠狠地说:“简直有辱斯文!”他不喜欢这种表面上的风光。也不喜欢这种他不认可的表彰形式,他把这种表彰形式看成是一种粗鲁和浅薄,甚至是侮辱。
还有一次,市里开大会,请他作佳宾。他不去,还说,当老师的,干嘛要参加这种无聊?哪还做什么学问?
他喜欢助人,这是他一惯的举动。但到了倒霉时,就没有这个能力了。但他对于讨饭的人,是一定要施舍的。一次一个乞妇抱着一个婴儿来讨饭,非常可怜,他立即拿出五元钱来给她。要知道,当时他家里已极端的困苦,那时的五元钱,一个人节俭点,可以过一个月。
余绾也很有趣,他和梅俞不同,是才子型的。
一次,学院里放电影,在礼堂。电影开映后,梅俞家的老四有事出来,看见余绾正偷偷地搬着砖头在黑暗里,然后靠墙坐下来。老四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余伯伯。这时,正好几个学生进来,看见了他。一见余教授竟蹲坐在地上,忙叫他坐到前面去。他忙挥手,叫他们前去。他喜欢这样的自在,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
还有一次,他和梅俞,徐晒到一小茶馆喝茶。他喜欢喝茶。说是喝到了好茶,就立即走到隔壁的杂货店,买了一个瓷杯,装上这杯好茶。小心翼翼地捧回家去。他就不知道向这个小茶馆买上几包茶带回去?何苦要这样辛辛苦苦地捧着一杯茶走回去?
这又引起了学院里的一些晚辈们的欢笑,然后是惊讶!
这也真是十分愚傻得可笑了,然而却是“是真名士自风流”。
2009-8-10
搜索关注 连城读书 公众号,微信也能看小说!或下载 连城读书 APP,每天签到领福利。
--------------------
大大加油~~好好看的文文!!!!!!!!!!!!!!!!加油加油!!!!!!!!!!!!!【img14】【img14】【img14】【img14】【img14】【img14】
--------------------
【img31】【img32】【img31】【img32】 加油写啊,第一次见的这么用心去写,好好看啊
--------------------
看了大大的文 感觉真的存在 好像走进了心里 能让人记住 好像成熟啊 不过很喜欢这种感觉 咱没这能力 只能羡慕了
--------------------
明月时时有,把酒不问天。 天上宫阙不知,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风奔去,又恐寒风冷云,高处无文看。 起舞伴君影,与你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我欲眠。 不应忘我,虽不见面月照圆?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不想全。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酸杏祝萍萍中秋快乐!
--------------------
因为最近很忙,做很多事,虽然说答应你的来回访,应该很认真地给你写书评,否则就是对你作品的不尊重,但我最近是真的很忙哦,所以有点抱歉了,忙过了后公子会认真地看亲的作品的,拜读大作了。
--------------------
非常沉厚的笔力,沉厚中又带有古色典雅的风韵,看的时候有些恍惚,像在翻一帧帧清晰而厚重的老照片,质朴的色泽,简洁而温厚的言语,让人在宁静的追忆中心生悲凉沧桑之感。真的很钦佩作者,深沉的情思阅历尽在笔下,单几个作品名字就让我沉吟许久,是如此贴切而富有内涵。很抱歉隔了这么久才看到大大的留言,早前在短文频道看到《落叶一首诗》的时候便对大大的名字有所留意,又看到大大在咱家许多作者文下都有留言鼓励非常感动!谢谢大大的支持,很喜欢大大的文笔和情思,期待创作更多更好的作品!O(∩_∩)O~
--------------------
确实有了阅历才会写出这样的文,很是深沉,有种让人透不过气的感觉。虽然不喜欢这样文,但是也别样的收获。
--------------------
看了你的留言,我便来看文,那是一种我们没法去身临其境去感受的时代气息,或许,对于我们来说,那就是很久远的故事,能够感受,可以感动,却永远没办法懂得透彻,理解真谛,但是我是个非常爱看故事听故事的人,那种淡淡却又凝重的感觉,让我心颤,所以,偶要追文哦~~哈哈,我喜欢看耐人寻味的文,会常来的,加油哦~~
--------------------
其实,也只是刚看了《假日车站》而己。平实,而又伤感。应该是有一定阅历的人才写得出的。…………………… 我在连城,是没想要看正经的文学作品的,纯是为了看一些古怪故事,放松心情。因此,光看简介就知道很沉重的东西,我基本不看——为了自己的健康着想…………………… 如果不是你在我那里留了印,我也没缘转到这里来。我想,你的年龄应该与我相仿,或许,可能比我稍大。因为,你的文字里,我闻到了那个年代的气息——那是年轻一辈模仿不来的气息。我也庆幸我来了,看一看连城里不一样的文笔。《车站》一文,跟我刚看完的一本朋友写的实体书的风格相近。都是用淡淡的语气讲述深情故事。只是,我朋友的故事更深,更长,更苦涩一些…………………… 也许经历过的,阅读过的东西太多,所以基本在开篇我就猜到了故事结局。但我依然看了下去,因为在文字,可以感受到含蓄的绵绵深情,和淡淡的剪不断的相思。愁在爱里裹藏着,苦涩卷在毫无恶意之中。看
--------------------
呵呵,谢谢你的留言~在茫茫书海中找到本姥爷~~ 祝你成功~~【img12】【img12】【img12】
Copyright 2024 lcdudu.com All Rit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未经许可不得擅自转载本站内容。
请所有作者发布作品时务必遵守国家互联网信息管理办法规定,我们拒绝任何反动、影射政治、黄色、暴力、破坏社会和谐的内容,读者如果发现相关内容,请举报,连城将立刻删除!
本站所收录作品、社区话题、书库评论及本站所做之广告均属其个人行为,与本站立场无关。
如果因此产生任何法律纠纷或者问题,连城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